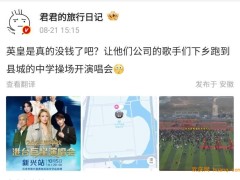“曹禺写《雷雨》时23 岁,温方伊写《蒋公的面子》21 岁。”温方伊是谁?《蒋公的面子》又是一部什么样的戏?拿温方伊与曹禺相提并论合适吗?
不管对比合不合适,对比与联想已成事实。当《蒋公的面子》走出南京大学校园,在上海演到该剧的第48 场,上海戏剧界的专家在演出结束后的学术研讨会上,自然提出了这一问题。
4 月3 日至6 日,话剧《蒋公的面子》在上海戏剧学院上戏剧场连演4 场,这是这部由南大在校学生温方伊创作的话剧,首次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公演,然而效果与在校园里演时一样火。用一票难求来形容似乎不为过。著名编剧赵耀民就对该剧的导演吕效平说,应该在上海多演几场,很多人因为没买到票,没看到戏表示遗憾。这部戏的魅力究竟在哪?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路生看完戏后,直呼“话剧回来了”,他把这部戏定位为“人文主义回归的文人戏剧。”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剧协副主席罗怀臻,甚至把这部戏放在中国戏剧走过百年之后的背景下,称之为“2013 年中国文化的传奇”。著名编剧贾鸿源在研讨会上对年轻的编剧说“妹妹你牛逼!”,他觉得这部戏很有冲击力,在上海的演出,撕破了上海话剧界的面子。
面子问题,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1943 年,重庆。蒋介石亲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吃年夜饭。这使三位教授很纠结: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1967 年,南京。三位教授为此事遭受审查,他们诚惶诚恐地回忆往事,真相难觅。”
简短的两句话,可以把《蒋公的面子》这部戏的剧情介绍,然而,介绍不出的是时间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情怀、风骨的种种变化。由“面子”入题,这出戏,讲的还是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的境遇、良知与颜面。它是对过往岁月的戏剧化再现,也是映照当下人文生态的一面镜子。这也是它能引发现场观众共鸣的真实原因,没有疑问,这部戏是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然而它能让观众想起当下的种种,这也是这部喜剧的外化与内在。它很好地抓住了我们时代的敏感点,做人,做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在哪?大幕起,简洁的舞台上,现出一桌三椅。暗淡的灯光映照,照出舞台深处的一幅对联:“自来自去堂前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人物依次出场,夏小山、时任道、卞从周、时太太,人物关系并不复杂,前三位都是大学教授,是同事,他们都接到了刚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的请柬,时任道痛恨独裁,不想赴宴,然而心痛自己远在桂林的数千册藏书,出于无奈,想请蒋发令,运回自己的书;夏小山是位“潜心学问不谈国事”的美食家,听说宴会上有道好菜,心动了;卞从周“支持政府愿意赴宴,却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故事就这样展开,简单的叙事,没有任何华丽的舞台效果,全靠对话与暗藏机锋的台词。
戏剧效果的推进在于很好地抓住了麻将这一道具,在时任道家中“打麻将”这场戏将剧情推至高潮,冲突毕现,心痛先生的时太太在剧中,也起到了粘合剂作用。然而戏剧引人入胜的地方,其实是将1967 年的场景与1943 年三位知识分子争面子的戏予以并置,如果观众不是一位笨蛋,都会产生自己的联想。
蒋公的面子,其实是知识分子自己的面子,给与不给,在不同的境遇中,成为喜剧的酵母,也成为悲剧的哀鸣。
话剧回来了,人文主义的文人戏剧在回归
就是这样一部剧情并不复杂,更没有玩任何舞台花哨的在校学生创作的话剧,在中国话剧界激起了波澜。在上海的公演,也引得了众多上海戏剧界的专业人士的赞扬。上海演出结束后,由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剧协副主席罗怀臻组织上海戏剧界的剧作家、剧评人、上戏教授、学者、戏剧人等开了一场“话剧《蒋公的面子》学术交流会”。他们的反映之大,可以看出,这部戏对上海话剧界的撞击与震动。一群话剧前辈,纷纷向年轻的编剧温方伊表达自己的“崇敬”。著名编剧贾鸿源在研讨会上对温方伊直言:“妹妹你牛逼!”,更有学者将温方伊与曹禺相提并论,把她比作中国话剧经过100 年的发展,看到的又一颗新星。而温方伊自己则认为,这部戏能给大家带来惊喜,在于当下好的话剧太少了。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韩生在研讨会上抢先发言,他觉得这是一部触及灵魂的戏。他说:开始就是未来,这部戏与现代社会的连接很好,很值得关注,值得研究,话剧是现时代的艺术,关注当下,关注历史,它做到了这一点。现在触及灵魂的东西很少,因为跟利益交织在一起。他觉得也为上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则认为,这部戏有价值观的思考,通过戏中的三位知识分子来告诉我们今天怎么做知识分子。剧场里有很多笑声,是从人物内心里发出的,不是外加的“无厘头的笑声”。话剧保证了最起码的独立性,不谈政治,但可令人产生丰富联想。没有把人物概念化,把人性挖掘了出来。
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路生则直呼“话剧回来了!”,他说,近20 年来,话剧变成了导演中心论,都宣扬和强调在以所谓创作坊的形式做即兴创作,不需要编剧了。但从这个戏来看,它真正体现了编剧作为话剧的主体,它就是一部真正说话的戏。是靠精彩的台词,与演员的对白来吸引观众的。这部戏可以说是人文主义回归的文人戏剧。但他也觉得,戏在处理事40 年代与60 年代的时候,两个部分的粘合力还不够。
撕破了上海话剧界的面子
如果说这部戏仅仅是局限于话剧本身,可能它还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这部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出自一位初出毛庐的学生之手,还在于它对话剧生态,对教育体制所产生的冲击力。赵耀民就认为,上海不可能出这样的戏。即便是有学生创作出这样好的剧本,老师最多给个分数,不可能自己组一个剧团,把它排出来。而南京大学相对比较自由。问题还在于制度。他说,这个戏如果在上海,也出不来,在老师这一关就给枪毙掉了。现在大多数学校的老师变成了技术工作者,学生自然没有原创力。他很欣赏温方伊的才华,但才华就是价值观。目前国内的很多剧,其实都是价值观的问题,论技术,并不比国外的差。我们看到这个戏,很兴奋,为什么?因为它讲真话,真诚,这应该是一个常态,但现在变成了难得的一件事。这是它对中国话剧逐渐失望的过程。他常在想中国话剧还有没有下一个百年,之前感觉难以为继,但看了这个戏有了点信心,这样的在体制外面的戏多了,再过一百年没问题,中国话剧的增长点就在这里。
贾鸿源则说得更尖锐,他认为这部戏演活了知识分子的异化,然而它的冲击力,更在于撕破了上海话剧界的面子,撕破了上海话剧光鲜的皮,是它对上海的戏剧环境的冲击。他认为上海的话剧界太郁于小圈子,缺乏情怀。
然而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一部冲破校园体制的束缚、被上海话剧界评价极高、在全国引起了众多媒体关注的戏,在第三届全国校园戏剧节上却落选了。该剧导演吕效平,谈起此事,很像个愤青。他说:“这个戏演到30 场,是江苏省的一个文化事件,演到50 场就是全国的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影响力才刚刚发酵,接下来它还将在北京、广州、深圳、西安、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南昌等城市巡演。我要让票房说话,票房就是力量。商业的成功是我的目标,我要证明国家化戏剧是错误的,我得改变国家这个戏剧体制。我反对戏剧被国家化。”
吕效平选择与国家化戏剧“死嗑”的姿态,或许让《蒋公的面子》也正在撕开中国话剧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