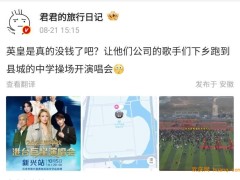很少有小提琴家能几乎不靠任何比赛的光环,就成为享誉国际的古典乐明星;也很少有小提琴家21岁时就创立了音乐基金会,投身于古典音乐的教育与普及。宓多里用自己的天赋与执着,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音乐之路,打破了年龄、种族、社会、地理的疆界。
在沪逗留的短短几天,宓多里频频现身多个音乐普及现场,从吸引了诸多中老年观众、白领的“音乐午茶”,到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天使知音音乐沙龙”,她以女性特有的天赋与柔韧,平和与博爱,征服了所有人。
乐于做普及
“剧场内外都能分享音乐”
记者:这次为什么会来?
宓多里:对于来上海,我一直很期待。演出前一天,我还参加了上海音乐厅的“音乐午茶”活动,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音乐的分享可以是剧场外,也可以是剧场内,对我来说,以不同的方式,和喜欢音乐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
记者:这次你带来了巴赫无伴奏奏鸣曲与组曲。有个传言,你8岁的时候,在家拉巴赫无伴奏奏鸣曲,你的母亲用录音机录下了这一段混杂着家中小狗叫声的录音,结果却让小提琴教母迪蕾听了大感意外。能谈谈在你不同年龄阶段,对巴赫作品的不同理解吗?
宓多里:直到现在,对巴赫的音乐,我都心存敬畏。事实上,无论你演奏过多少次,听过多少次,巴赫的音乐总让你觉得还是无法穷尽的。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总觉得自己和巴赫的音乐有着特殊的连结点,尤其是他创作的小提琴独奏作品,它们蕴含的情感的诸多层次、细节,只有在经历过人生无数的学习、表演之后,才会在你的内心“显山露水”。
谨慎说普及
“普及给了大众学习机会”
记者:你21岁就创立了“宓多里之友”基金会,致力于古典音乐的普及和教育,给那些没有机会接触音乐的小朋友,带去了广泛的课程、音乐会,能透露一下,是什么促使你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宓多里:在我成为演奏家的30年里,大概有20多年,我持续不断通过一个或多个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很想将之融入到生活中,当然,家庭环境、个人兴趣以及周围朋友的鼓励,促使我下决心成立这样一个组织。
记者:21年间,“宓多里之友”去过哪些地方?最让你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宓多里:成立至今,“宓多里之友”的活动主要聚焦于纽约,当然,通过和不同组织的合作,我们的脚步也有幸延伸到了其他地方。至于最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很抱歉,我从来不爱分享这些私人的体验,我希望能把这些记忆留给自己。
记者:艺术普及和教育,在你看来,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宓多里:音乐普及不是为了让音乐更流行化,而在于给大众学习的机会,这种影响将是潜移默化的,会带来许多积极的效果。
谢绝给建议
“每个琴童都独一无二”
记者:在成为职业小提琴家之前,你选择在纽约大学学习心理学,而不是音乐学,这样的选择对你的音乐之路有什么帮助?对于一心想要走独奏家或是艺术家之路的琴童和家长,你会有怎样的建议?
宓多里: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对大学生活十分向往,可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进入纽约大学Gallatin学院上课时,我仍然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学什么专业。按照原本的设想,我应该会主修艺术史或是文化研究之类的课程,但上了几节核心课之后,我知道自己错了。像当时许多大学生那样,我选上了各学科的一些核心课程,一次正好是介绍心理学的课,我一下被吸引住了,对人类思想以及互相影响的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深信自己想要投入学习这个领域,后来如愿以偿,主修“性别研究”。
的确,我经常会被问到,是否能给琴童或家长一些建议?但其实,这是非常无礼的要求,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来说,成功的意义不尽相同。所以,我不会给出所谓的建议。
记者:你曾说,刻苦学习并对音乐充满感激,是你在幼年学琴过程中学习到的两个关键点。对爱好音乐的孩子们来说,你觉得该怎么做,才能让音乐成为生活的乐趣?
宓多里:对音乐充满感激和刻苦学习,两者是互相影响、彼此延伸的过程。当然,对任何一个演奏者来说,年复一年学习规则、练习乐器的过程都是困难的,但这种坚持不懈,必将带来丰裕的成果,这种成果不仅在于演奏者能更好地通过音乐表达自己,更在于他对音乐其他方面的理解也在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