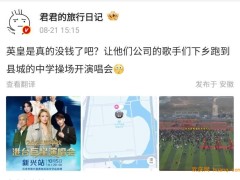5月5日、6日,《蒋公的面子》巡演至深圳,迎来它的第54、55场演出。这部由“9 0后”在校生温方伊编剧、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执导的话剧,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在深圳的演出,同样成为文艺界的话题热点。5月7日,南都全媒体集群与欢庆网联合在深港人文生活馆举办了《蒋公的面子》研讨会,该剧导演与深圳本土的资深戏剧工作者、剧评人、文化学者会聚一堂,以《蒋公的面子》为引,就学院戏剧的市场化操作途径、中国戏剧发展现状、如何突破国家化戏剧等问题展开探讨。这是冲破“面子”的一次戏剧外延,也是对深圳戏剧生态的一次话语撞击。
0 1这是一部从严肃到荒诞的戏,它的深刻性烙在观众的心里
《蒋公的面子》的剧情围绕这样一段轶事展开1943年,蒋介石初任南京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夏小山、时任道、卞从周)共进年夜饭,这使教授们非常为难,为此他们争吵了一个下午: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这个剧情,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下,面对强权时的纠结困境把眼光投入当代,当下的知识分子处在什么样的人文语境之中,他们之间应当缔结什么样的关系?而学院性戏剧能否为当下的知识分子找到自己新的定位?
冷炳冰:《蒋公的面子》这个剧本非常有意思,它包含了很多黑色幽默,节奏把握很好。关于面子,它阐述了一个“面子理论”,你要别人给你面子,你就要给别人面子,你要想保存自己的面子,一定要保存别人的面子,你要想伤害这个人的面子,最终结果是这个人一定会伤害你的面子。其实这三个教授,见不见蒋公,就是我给不给蒋公面子,其实当中还有知识分子我自己面子的问题,剧中教授的面子,就是文人的面子,还涉及到保存面子的礼仪和文化。
邓康延:知识分子最向往的,就是百家争鸣、各花齐放的时代,从《蒋公的面子》中,我仿佛看到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时而自信洒洒,时而卑微渺小,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黑色幽默”。而近年来,许多戏剧活动以分散状态,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着,它们让人看到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力量在集结、凝聚。戏剧活动,通过微博及其他新媒体在持续发酵,这是新媒体同样发达的其他西方国家都未曾有过的现象。当代知识分子正在用“文艺”重建风骨和气节,未来的时日里,不仅仅是话剧,电影、纪录片、音乐、美术等各个方面,都会迎来一个大的拨乱反正,都会将知识分子个体的微型力量、呼吁“自由”的声音片段集结起来,最终令文化生态产生裂变。
陈皮:怎样给“好戏”下一个定义?所谓“好戏”就是“你台上演的,你说的,我台下听着,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而且能说到我心坎里去,是我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政府体制下的戏剧过于走高、大、全,所以它吸引不了观众。《蒋公的面子》真正体现了导演吕效平“戏剧就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的见解,教授的纠结就是烤灵魂,再加上历史、文化、生活的佐料,不但最瞧不起俗货的文人受用,广大看客一样受落。很多戏像小丑一样乱堆砌别人的外延,《蒋公的面子》却像戏曲中周正的正旦。是一部真正有养分有氧气的好戏,我很认同这个说法。
程勇:我觉得《蒋公的面子》是一部虚构到真切的戏,是一个捕风捉影的历史故事,呈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关于面子和理智,关于架构梦想和犬儒血液的关系,还有关于对于情操的追求和在利益面前妥协各种的面孔和纠结。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特有的聪明与滑头,这是一部刻意到随意的戏,无论是台词、台风表演都在刻意地呈现民国的味道和风范。因为整个剧情结构完美的起承转合,还有演员精湛的表演,处处随意,一气呵成,130分钟确实是全程都是亮点,这是一部从严肃到荒诞的戏,戏的主题非常严肃深刻。比如,“打麻将不可三缺一,但是赴蒋公的宴是不可一缺三”等台词,荒诞化地呈现上来,让这种深刻性更加烙在了观众的心里。尤其值得喝采的应该是导演最后上台的一番演讲,
我甚至认为这是整部演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看完戏所积蓄的情感与思恋,被导演的一席话点燃,全场观众因此热情澎湃,效果是非常棒的。
0 2《蒋公的面子》让人们看到“学生杰作”的巨大潜力
最令人惊叹的是,《蒋公的面子》牵涉多个复杂史实、人物性格刻画精到深刻的剧本,竟然出自南京大学“90后”在校生温方伊之手,这也让与会嘉宾们陷入深思原来,中国戏剧原创领域并不缺乏少年早慧的人才,以此为参照,当下中国戏剧的学院力量、后继力量到底有多少,如何充分发掘?“校园戏剧”究竟能有多大的生命力?
冷炳冰:《蒋公的面子》这样优质的剧本竟然出自一个“90后”学生之手,这十分令人惊叹。这也说明,戏剧行业的青年后辈正在崛起。而除了编剧之外,在各种戏剧舞台中,也常常能看到学生演员的风采广播学院的、戏剧学院的、电影学院的,各种学生演员交织在一起,他们的演技还稍嫌稚嫩,并没有专业演员、文艺团体资深演员那么驾轻就熟,但他们这种“原生态”、粗放状态却更让人们看到可贵的潜力。他们相对粗糙的舞台表现、动作、台词处理,恰恰有一种可贵的味道。
“学院派”味道应当被延续。与南京大学相对成熟的戏剧文化相比,深大的剧场还没有成熟的运作模式和制度,市场化程度也很低,但这并不表明深大的师生没有优秀作品。当下的戏剧公司、出品方应当多关注这些活跃在基层校园中的作品,把它们采购过来。这些学生作品往往也有很大的潜力。
吕效平:很多戏剧青年才俊正在高校里渐渐成长起来,譬如,写出《蒋公的面子》的温方伊,在南京大学并不是唯一的人才。近年来,南京大学里涌现出很多优质的剧本、创作成果和小型演出,几乎每一部都能掀起对文化、家国、现状的批判和反思。这也让人们看到“学生杰作”的巨大潜力。学生的创作力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高。
0 3 这出戏让人看到中国话剧在经过百年的发展后,还有新的生长点
戏剧的市场化逐年更新、升级,独立戏剧、先锋戏剧越来越多,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行政、资本上更为强势的“国家戏剧”、“官方戏剧”,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会导致何种格局?当下时代,戏剧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传播工具,而更多地与大众娱乐贴近,这种环境能否促使戏剧的艺术属性更加纯粹地释放开去?“国家化戏剧”能否被瓦解?
谢湘南:现在很多戏,定位是市场化、商业化的,但它们的问题是过于娱乐化,《蒋公的面子》是对过于娱乐化戏剧的拨乱反正,现在很多戏剧的创作采用的是“导演工作坊”模式,都是以导演现场制作戏剧的模式来进行集体创作,它更多是一个创意的集中体,《蒋公的面子》还是沿袭了话剧本身的创作方式,它是真正从话剧的本体,从剧本出发的,这种话剧艺术的探索更本质地呈现了说话,呈现了语言的趣味与魅力,也是对现在正在流行的导演中心制戏剧的反叛。这是从话剧本身,从中国话剧百年发展至今天的大背景下,来谈它的意义与价值。当然,这部戏最大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它对国家话剧体制的冲击,它提供了体制外话剧创作的一个生动样本,它让人看到中国话剧在经过百年的发展后,还有新的生长点,它让话剧恢复其本真的涵义。
吕效平:戏剧要充分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行政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创作、公司创作、学院创作,要形成自己独有的市场竞争力,才有资本和官方抗衡。近年来,官方经常拨款做戏剧,但很多所谓的“作品”实际上特别主旋律而且说教,宣传的都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东西。正确的做法是,官方充分放权给民间,放权给专业戏剧机构,让各家呈现“百家齐放”的状态,戏剧就一下子繁荣、辉煌起来了。我一直有个理想跟国家化的戏剧死磕到底,死磕到这个制度发生反思、发生蜕变,我最大的优势是,我有学生,我有硕士生、我有博士生、有本科生,他们将来都会成为“死磕”的力量。有人曾悲观地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就是要一步步重新找回戏剧的尊严。
0 4 深圳戏剧界还没有“面子”,《蒋公的面子》可作借鉴
近年来,深圳、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均积极发展本土戏剧市场,由于各地政策、戏剧票房、观众构成等指标不尽相同,也产生了成色和形态各异的地域戏剧文化。那么,各地的戏剧发展可以互相借鉴什么?地域交融、互补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吕效平:深圳有天然的文化弱点,但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南京比较,南京是六朝古都,是民国首府,类似这样的“历史”深圳都没有。但是,深圳最大的特点是,全国各地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带着梦想和野心的人,怀着强烈的奋斗冲劲聚结到此。《蒋公的面子》能在深圳演出成功,取得这样的口碑和认可度,一方面在于深圳较为开放的戏剧市场环境,这也让我坚定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时上海有一家更大的演出公司来谈合作,但他们的做事态度却更加官僚、体制化,有一种“吃定”的店大欺客心理,但这种状况,在深圳却是看不到的,深圳有更强的包容性。
谢湘南:我在上海采访《蒋公的面子》的时候,上海举办过一个学术研讨会,满堂都是专业研究戏剧的教授,但是对比之下,深圳很难找到真正研究戏剧的专业人士,虽然深大也有,但是就今天的现场来看,能来参与关于戏剧研讨的很少。当时我的稿子里有一句话《蒋公的面子》不仅是撕破了上海戏剧界的面子,更是撕破了中国戏剧界的面子。那么相比较之下,深圳戏剧界有没有面子?这种对比就更有意思,或许,深圳戏剧界还不存在“面子”的问题,因为连戏剧研究的团队、戏剧的氛围都没有形成。
冷炳冰:近年来,深圳政府、文艺部门都在努力推广戏剧、花钱做演出。而从《蒋公的面子》的上座情况来看,我发现深圳观众的欣赏口味、文艺诉求一直被低估了原来很多人对文艺的欲望到了“求知若渴”的地步。这会形成一种倒逼,深圳的文艺家应该生产、引入更多的优质作品,把精品带给观众。
在中国全境之内、中西方交融最好的地方,具有样本意义的地方就是香港。深圳的艺术家、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到香港去学习,把香港的样本意义和价值借鉴过来。而在“培养观众”方面,香港做得更好。香港政府要求小学生、中学生每年、每学期必须看多少场演出虽然孩子可能什么都看不懂,但这实际上是在培养未来的观众。在香港,经常看到一些外语类的先锋小众戏剧,连很多小学生“粉丝”背着书包来看。另外,香港方面在打造“精品戏剧”方面也更为出色,因为当地的机制,是用市场来检验作品成色,决定作品生死,但我们内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常常是政府牵头主导,以行政力量打造所谓“精品戏剧”,花了重金却不一定起到理想效果。另外,深圳本土的戏剧文艺评论家力量也有限,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
《蒋公的面子》是把南京的戏剧带到深圳来演,未来,深圳的戏有没有可能带到其它城市去?深圳的戏剧界可以借鉴《蒋公的面子》团队的运作模式,用企业商业的规律来操作戏剧,提升采购力量,按照市场的标准择戏选戏,有朝一日,深圳的戏剧力量才能真正发展成熟。
出席嘉宾
吕效平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冷炳冰 深圳文联副主席
邓康延 深圳文化学者、纪录片制片人
南岛 南方都市报深圳杂志部主任、深港人文生活馆馆长
陈皮 资深剧评人
谢湘南 南方都市报文化编辑
程勇 《华商报》文化新闻部主任
童立 欢庆网市场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