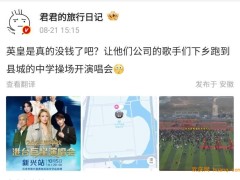早在4年前,“天下成都”的“成都骄傲”系列就以整版篇幅采访报道过宁峰。时光匆匆,如今已迈进而立之年的宁峰在事业、人生上又有怎样的感悟呢?在“宁峰2012中国巡演独奏音乐会”举办前,记者电话采访了远在德国柏林的宁峰。
我们相距7个小时的时差,但听到来自家乡的问候,宁峰显得很高兴,说话的语速十分从容。他回忆起4年前自己在成都举办演奏会的一幕。他坦言,其实自己每年都要回到成都母校看望老师、朋友,也参加过川音院校举办的音乐会,在成都举办对外的个人演奏会,这是第二次。
2010年春节前夕,宁峰与有“钢琴公主”之称的青年钢琴演奏家陈萨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参加了“龙凤呈祥·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音乐会。宁峰演奏了两首中国民族音乐作品《新春乐》和《牧歌》,一首欢快炫技,一首深情舒缓,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曲子,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宁峰在技巧和艺术理解方面的独特造诣。我看了电视转播,发现宁峰长得很像曲学大师卢前。当时他身着雪白的唐装,在演绎西方弦乐的领域显得特立独行。谈到这样的穿着,宁峰说,回到祖国就等于回到了母语文化的气场,一身唐装恰能与浓郁的春节氛围吻合。谈到这次他的个人独奏会,他说,穿着不会很刻意,符合自己的心情就好。
谈到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人演绎西方弦乐,宁峰说,“首先我经常对别人说,我是四川出来的,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但是我从小到大就没和大熊猫照过相。也就是说,身边的东西也许反而不重视。同样的道理,在欧洲,管弦乐是从他们那里生长出来的,但目前,在欧洲学古典音乐的亚洲人比欧洲人多。他们也许觉得自己的东西,不是好稀奇,很多人到中国学二胡,琵琶,因为他们没有。第二,音乐本来就是世界的东西,是一种语言,你一旦学会是不受限制的,没有什么国籍分别。当你学到一定境界以后,你不会太在意这个作品是一个德国作曲家的还是一个法国作曲家的,你只在乎把这种语言讲好。如果有人评价你的演奏风格还比较"中国化",那是一个比较委婉的低级评价。你演奏到一定高度,别人不会把你当哪国人看待,只在乎你拉得好不好。一句话,看你是否把别人对作品的期待完美展现出来。”
宁峰说,但愿通过这次回到家乡举办的独奏会让细心的听众感受到他4年以来的变化。“这是接受家乡的"检阅"啊,但愿他们能喜欢,我就很满足了。”
实录
一个大城市,需要懂严肃音乐的耳朵
“炫技”不是只重技法而弃内涵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一直以激情、炫技的演奏和独特的魅力著称。我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你演奏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很感动。一个内行对我讲,极为舒畅的运弓,无可挑剔的技术,具有感人的音乐表达。后来你携手广州交响乐团,演奏过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时你“告别”了激情炫技,让音符化作一分浪漫柔情。你心目中的“炫技”是什么?
宁峰(以下简称宁):要全面理解“炫技”一词。2005年我曾经出版的CD的确叫《炫技燃情》,那是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但这里的“炫技”,并非只注重技法而抛弃了内涵。“炫技”这一个说法,其实更多地暗示了我对演奏技法的重视。所谓“炫技法”这个提法不妥当,因为我演奏的小提琴必须服务于音乐,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技法。否则,就等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
其实,纵观音乐史,伟大的音乐家的技法必然是一流的,他们已经从优秀的演奏家上升到大师的境界。所以,一个学习器乐的学生,必须刻苦学习技法,方可谈音乐。就像一个好的厨师,你总不能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好菜。
记:所谓“炫技”并非仅仅是激情的唯一表达方式。
宁:是的。演奏家一生中会有不同的阶段,从童年直至中年,不同阶段的心境、情绪不同,对同一首曲子的理解也会悄然变化。我演奏的作品我会录下来,自己反复聆听,不但可以发现演奏中的问题,而且逐渐可以发现自己心情、理解方式的变化。
演奏家就该成为真正的音乐家
记:你曾经谈到,很钦佩前苏联小提琴大师大卫·费奥多洛维奇·奥依斯特拉赫,你认为从技术上来说他不是顶尖的,但从性格上来讲你觉得他和你最合拍。这是基于什么理由?
宁:奥依斯特拉赫5岁开始学琴,他的技法与风格十分迷人,他可以在同一个乐句中有些音符用揉指,有些音符不用揉指,两者没有中间的过渡层次,这种拉法跨越国界,在当今许多年轻小提琴家身上普遍存在,但只有奥依斯特拉赫处理得十分精湛。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人格感染力量,这才是大师所能拥有的。
记:奥依斯特拉赫后来也尝试过指挥。你考虑过在演奏之外,从事作曲、指挥一类的发展吗?
宁:的确没有考虑过。在20世纪前,很多演奏家与作曲家是可以合二为一的。诸如巴赫、莫扎特、肖邦等,他们既是一流的演奏家,也是一流的作曲家。到20世纪开始,作曲与演奏就逐步有了分野。发展到现在,演奏与作曲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如果说最大的音乐就是交响乐的话,那么,一个演奏家必须要把百分之六十或者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才能较为深刻地理解作品。既然如此,他怎么还有精力来尝试作曲或指挥?
记:所以有人说,19世纪是作曲的世纪,20世纪是演奏的世纪,21世纪则是聆听的世纪。你如何看待演奏家的艺术生命?
宁:中国人眼里的“音乐家”高不可攀,非德高望重七老八十,极少数人敢称自己是“音乐家”。如果有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的理想是做一个音乐家”,那是会遭人诟病的。但不要怕,追随理想没有什么错啊。演奏家就是应该成为真正的音乐家。可是演奏家随着年龄增长,中年后他的演奏会越来越吃力。技法会随着肢体反应能力的下降而下降。我觉得一般规律是,演奏家到了45—50岁这个年龄段,这种退化就来临了。
让《梁祝》符合西方“语法”
记:你与众多国外音乐团体合作,你在西方演奏过中国乐曲吗?
宁:我在荷兰海牙等地演奏过中国的小提琴名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效果很好,很受听众喜欢。今年2月,德国“中国文化年”在柏林宪兵广场音乐厅成功举办,我演奏的依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观众一波又一波的掌声中,我只好一再加演。作为音乐的国度,德国人对音乐演奏的水平十分挑剔,但中国爱乐乐团和华人艺术家联袂向德国观众奉献的这台精彩演出,赢得了德国观众极其热烈的赞誉。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梁山伯与祝英台》无论在和声配器还是编曲的结构方面,都符合西方的“语法”,主题又是爱情,西方听众借助于此,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感情。
记:我注意到你即将开始的2012中国巡演独奏会的节目单,你准备了两套曲目:在北京、上海、武汉演奏的均为外国名曲,在广州、深圳、成都的演奏会则安排了中国作曲家陈钢的《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和秦咏诚的《海滨音诗》,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宁:我半年前就在北京演奏过,总不能继续炒冷饭吧,所以需要安排新的演出曲目。其实,选择这些曲目,我花费了很多心思。在北京、上海、武汉演奏的曲目固然是名曲,但通俗点说,都是一些非常有内涵的精致的小曲子,不是大作品。而在广州、深圳、成都的演奏会使用的曲子,我更多地结合了这些城市的文化与接受能力,绝对没有谁高谁低的意思。
我曾有一个比喻,那就是面对不同的曲目,就像我在学生时代那样,我既会认真阅读古典名著,也会对《故事会》发生浓厚兴趣。这固然是两种文化的演绎,关键是你是否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有新的感悟和心得。所以,我很想把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品介绍给听众,这对提升一个城市的音乐文化素养会有所帮助。一个大城市,需要懂严肃音乐的耳朵。
对苦学琴童的两点建议
记:就你的经历而言,也是从琴童开始自己的音乐生涯。现在仅仅是成都估计就有上千名苦学小提琴的“琴童”。你对他们有什么祝愿?
宁:我有两点最深的体会,一是不管你能干什么,日后能走上演奏专业的必然是极少数。既然从事音乐,你就必须发自内心地喜欢音乐,而非仅仅出于父母的逼迫。要记住,热爱音乐,认真演奏。不要跟别人比,记住你永远要超越的就是你自己,去做自己能掌控的事情,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曾经坦言,在学生时代,我6年来就是以一个小提琴学生的身份不停地参加比赛,这促使我逐步意识到,我的目标是向艺术家发展,走上职业演奏家的道路。第二,无论你以后是走上专业的道路,还是成为业余爱好者,基本功必须打好。不需要非得给自己制定一个修建一栋50层大楼的宏伟目标,有很多事情不是纸上蓝图。一旦你能力、机缘等不够,就成危房了。与其非要修建这50层大楼,不如踏踏实实建造只有5层的“安心工程”。
说实话,我就是小学5年级立志要当“小提琴家”的人。但是怎么走,音乐家到底干啥,小时候谁想得出来啊!我的父母没给我什么压力,有两个表兄,在我选择读附中前,一个在考高中,一个准备高考。在题海中生活,我一点都不想经历。我决定绕道而行。
而立之后感悟音乐人生
记:可以谈谈你目前在柏林的生活吗?
宁:因为与世界各地很多乐团合作,我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过,平时相当忙碌。我一直在路途上奔波,但还是不大适应坐飞机十几二十个小时,这种漫长的旅途,想起来都让人头晕。一些音乐家天生喜欢这种生活,很享受这种环绕世界的生活,国际化的大舞台。鲜花。掌声。我并不天生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我想,如果这是每个音乐人生涯中必须完成的一部分内容,我也只好去努力适应……
哦,对了,与4年前在成都演出那阵不同的是,我已经成家了。夫人是华人,目前也在柏林音乐厅交响乐团工作。我们生活得很融洽,也曾同台演出。比如我们同台演出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大提琴双重协奏曲》,这是勃拉姆斯最后一部协奏曲,达成了小提琴、大提琴两种独奏乐器的精美协调以及和管弦乐的浑然一体化。
记:迈进而立之年,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
宁:总体而言我是幸运的,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在人生的某个关头,总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助我一臂之力。很多音乐家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经历会帮助自己成熟,可以更豁达地看待成功与失败。所以,我未必就“立”起来了,这需要经过更长时间来评价自己。一把提琴走天下的岁月,让人感慨不已……
记:奥依斯特拉赫曾这样描述他的发现:“音乐如同沿着一条美丽的河流顺流而下,突然间,我们发现大海就在前面。河岸渐次退向远方,你可以向四面八方瞭望,这时候有无限多的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
宁:哦,透过琴声,我看见大海。
(来源:成都日报 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