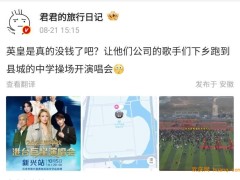王珮瑜——她是电影《梅兰芳》中为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配唱的人,她在戏迷中有着“小冬皇”的美誉,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她还是沪上最“酷”的青春京剧偶像,拥有点击量很高的个人博客……这个从苏州走出的书卷气极浓的女孩,本应是温婉、娟秀的江南小女子,却在舞台上以女儿身演绎男子百态。
虽然身量比男演员小了一号,但她的演唱中气十足、满宫满调,气质上的沉静从容更是颇有大家风范。继上个月在梅兰芳大剧院举办个人专场之后,6月5日晚,她将挑梁《珠帘寨》,为长安大戏院十大流派新秀的展演收官。
■“不做孟小冬第二,要做王珮瑜第一”
回首往事,她不禁感慨当时的年少无知
去年12月21日,王珮瑜在上海为纪念孟小冬的活动登台演出《乌盆记》,那天恰逢“冬至”。前一天,剧组同仁冒雪到“冬皇”曾居住的居士林遗址前上香,用硬币占卜“冬皇”是否来看戏,连问三次都显示“来”,于是他们给王珮瑜发短信说:“明儿,冬至。”
事情要从当年谭元寿一句“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说起——那让王珮瑜的艺术道路陡然开阔,从此,她便与“冬皇”有了缘分和默契。
“那是在1996年,我还是戏校三年级的学生,一次,谭元寿老师看过我的戏后,说了句‘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后来我明白了,拿一个戏校还没出科的孩子和大师相比,其实是老师给一种舆论,如果当年没有这句话,我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而有了这句话,我便跳跃式地进了京剧殿堂,现在想想,这么多年来真是受之有愧。”
不过当年尚未毕业、意气风发的王珮瑜并没有完全领会谭先生的苦心,面对“小孟小冬”的美誉,她竟然“狂妄”地说“我不要做孟小冬第二,我要做王珮瑜第一”。五年后再回头看这个称呼,王珮瑜不禁感慨当年的年少无知。“如果真能成为孟小冬第二,那何尝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呢!想通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无论对于艺术还是人生的理解都上了一个层次。”
如果把这样的变化称作王珮瑜成长的第一个阶段,那么此后她又经历了艺术修养逐渐沉淀的第二个阶段——做王珮瑜第一容易,但做孟小冬第二,甚至余叔岩第三却太难了。“这需要你先踏踏实实做一个继承者,于是我跟老艺术家开始了抢救式地学习,不一定今后要唱,但一定要先装进自己的兜里。只有先把自己充实了,才有资本把这些东西拿来自己用,总是跟着别人,无论如何也走不远。”
“小孟小冬”的称呼,也让王珮瑜和谭元寿成了“忘年交”,如今,几乎每次王珮瑜来北京,都会到谭先生家拜访,而谭先生对她也是倾囊相授。他希望能把当年谭富英跟余叔岩学的《定军山》和《战太平》传授给王珮瑜,能唱最好,即使不能唱也要把它传下去。
为电影《梅兰芳》中的孟小冬配唱《游龙戏凤》,给“小冬皇”王珮瑜又添了一把火。去年12月,《梅兰芳》首映后的第二天,等待了一年多的王珮瑜自己买票走进了影院,一向对自己很苛刻的她,自我评价是发挥得不错。另外,她自然对孟小冬这个人物的处理最为关注:“梅孟的情感处理很含蓄,对孟小冬没有任何的玷污,章子怡的形象很清秀,能够感觉到她很用心地去贴近老艺术家的做派。不过唯一遗憾的是章子怡的形象与我的声音有点配不上。但是我和葆玖老师的合作单从音乐角度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影片结束字幕滚动时,王珮瑜听到后排的观众在小声议论,“你看我说是王珮瑜配的吧。”一句简单的对话,无疑是对她最好的褒奖。
虽然为《梅兰芳》配唱仅仅是王珮瑜从艺道路上的小插曲,但她对每一次与观众的“对话”,哪怕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谋面”,都丝毫不敢懈怠。“观众对你的期望是很高的,我也希望自己能与这样的期待相匹配。刘曾复老师(有京剧通天教主之称)曾经对我说,‘珮瑜,你也30岁了,以后千万不能乱唱,有底的你唱,拿不准的一定要问老师。你已经成了一个参考的范本,唱戏已经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所以一定要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做好唱戏这件事。’”
■工作室这条路没有错,只是当年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市场的水有多深
对于很多北京的戏迷来说,熟悉王珮瑜其实是从她离开上海京剧院,成立工作室开始的。2006年,上海《新民晚报》突然登出一则消息,称王珮瑜“扔掉铁饭碗,誓死不回头”。那时,25岁的她已经是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了,可在这件事上,她没和团里打招呼就先跟媒体讲了,在上海文艺界掀起了不少涟漪。虽然后来工作室无疾而终,但她至今认为工作室这条路并没有错。
“这种形式对于从业人员来说是很健康的一条路,但就目前的局面来看,靠几个人的力量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很难支撑。梅兰芳先生当年是角儿里面戏班最大的,最多时也没超过21个人。要撑起一个很大的场面,管理经营团队是最重要的。开始时,很多人都来劝我,但我必须到黄河,否则我不死心。也有很多人说我无知,或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我也不想荣华富贵,我就是想唱戏。可当我真正走上了市场才发现,原来所有要打交道的人都是体制内的,我最大的困惑是我要唱戏还是要管经营,这对矛盾似乎没办法克服。有一天我想明白了这件事,一晚上都没睡着,原来那段时间是我把自己给孤立了。”
想通了这个,王珮瑜又陷入了另一个困惑:“回到剧院,承认自己失败倒是小事,我知道跟领导一通嬉皮笑脸,人家不会拒绝我,但我是选择仍旧棱棱角角地在那里支撑着,还是在团里装孙子呢?”在考虑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一早,她回到京剧院找到了院长,表达了自己想回来的愿望,于是,王珮瑜在别人眼中“瞎折腾了一通”之后,又回到了体制内。
“这件事让我一下子就成长了,你是一个演员,你有经营思路没错,但你没这个能力,在这个年纪做这些事是成功不了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仍然有成立工作室的理想。过去不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了这个市场的水有多深。那时我处处和京剧院作对是不对的,京剧界论资排辈的现象肯定存在,老师们拿我当晚辈、当学生也很正常,我在尊重老艺术家的同时,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想想,当初工作室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占了媒体很多的版面,也抢了很多人的风头,这都是自己的失误造成的。”
■京剧也需要生态保护,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去浪费国家的钱
我们所熟悉的京剧大家,无一不有自己的代表剧目,然而对于现在的京剧演员来说,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剧目似乎已成了奢望,身为上海京剧院演员的王珮瑜同样面临这样的尴尬。“拥有自己的剧目是需要机会的,你有意愿,还要看剧团是不是有可能,还要找人写,找人导,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从学校毕业八九年了,几乎没怎么期望能够排新戏。”
在她看来,能够把骨子老戏唱出新声音来就不容易了,而且自己也没到拿来个本子就能当半个导演参与二度创作的程度。王珮瑜说:“我的艺术造诣还没到那个火候,因此我不能拿自己的无知去糊弄观众。我知道这样说会打击一批演员,但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也许明年我会有新的尝试,但我不会用别人的投资,服装都可以不用新的。京剧也需要生态保护,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去浪费国家的钱。所以我会自己出钱,只有这样才能拿它当自己的羽毛一样去珍惜。”
其实很多大企业家都是王珮瑜的朋友,但她从不向他们开口,甚至没让人家冲自己的面子包过场,哪怕她面对的剧场里只有5个人。“你看人家张火丁、于魁智,贴什么戏什么戏满,我跟他们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至于找人投资排戏,我首先要付出,让你看到京剧的好,看到这门艺术有文化潜质和商业价值在,那时我出艺、你出钱,我们共同做一件事,我不是索取。”
如今,王珮瑜一年的演出有近30场,这在京剧演员里已经算多的了,只要环境允许,一旦找到她,无论报酬多少,她都会答应。虽然已经是挂头牌的演员,但她一直觉得:“少了你照样开锣,你牛什么呀。”于是,当团里给她重要的角色时,她会竭尽全力,即便是团里不太重要的日场演出,她也愿意演个角色。
■无论女老生还是男旦,千万别把自己边缘化,不要老把困难挂在嘴边
多年顶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的头衔,王珮瑜在戏曲界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但她一直忌讳人们把“女老生”挂在嘴边。“虽然我是女的演男的,但我一直用一个京剧演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不希望别人总是认为女老生不容易,以此来原谅和接受我的不完美,总提女老生会把自己边缘化的,这样的评价我不要。”
当年,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合作一直被视作梨园佳话,女老生和男旦这种看似错位的组合也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审美感受。当今京剧界,女老生和男旦可谓凤毛麟角,仅有的几个演员间也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惺惺相惜。近两年,国家京剧院的两位男旦刘铮和杨磊十分活跃,王珮瑜也非常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其实男孩唱旦角,比女老生的生存环境还要恶劣。我们聊天时,我常常说千万别把自己边缘化了,不要总强调自己是男旦,不要老把困难挂在嘴边,剧团里的龙套演员比我们苦多了,而且这个行业本身就很困难。媒体上也不要总说我们是多么的举步维艰,一个男孩子在舞台上把女孩子演得那么传神,而他生活中又很时尚、很敬业,这多好啊。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好,要让大家看到,我是唱戏的,我很快乐,我也开车、住别墅,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很会生活。”
生活中的王珮瑜总是很酷,一副中性时尚达人的装扮。她希望改变人们头脑中京剧演员总是土土的、很板正的印象,而且她看重的,不仅是外在的形象——
陆地园,这是一个正逐渐被人们遗忘的名字,2006年12月26日,这位曾经的“四小须生”之一英年早逝,18岁的年纪令人扼腕。为了挽救他的生命,艺术界举行了若干次义演,其中2006年3月4日在解放军歌剧院的那场义演,就是由王珮瑜发起的。为了有尽可能多的票房收入,3月1日,王珮瑜只好自己去跑票,然而一天下来却收效不大,她急得坐在北京的街头哭泣,想起自己冒着大雪去卖票的情景,再想想京剧界一些有影响的人反而不积极,她第一次尝到了寒心的滋味。“我们这个队伍对于社会和公益的付出太少了,一心只想着拿‘梅花奖’,参加‘青京赛’……不仅仅是唱戏而已,我们也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有好的社会形象。”